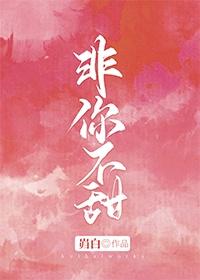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>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(第3页)
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(第3页)
“闻”
苦笑,“可惜太迟了。
三十年的遗忘,已经让三代人断了根。
重建比毁灭难十倍。”
两人并肩坐了很久,直到夕阳西沉,将驿站残墙染成血色。
入夜后,他们在废墟中升起一堆篝火。
火光跳跃,映照出彼此苍老的轮廓。
“闻”
从包袱里取出一本薄册,递给阿启。
“这是我整理的《归名实录》,记录了近三年各地自发举行的‘归名礼’。
有些地方,一场仪式找回了七十二个名字;有的村子,连族谱都被烧毁了,只能靠老人口述一点点拼凑。”
阿启翻开一页,只见上面写着:
>**凉州陈家屯,甲辰年清明。
>仪式由八岁女童主持,因其梦见曾祖母托梦诉冤。
>据其描述,曾祖母名唤柳氏,十九岁嫁入陈家,因不肯交出藏粮,被批斗致死,尸体抛入枯井。
>家族原不知此事,经核查旧档案,确有记录。
>当晚,全村燃灯三百盏,置于井口,诵名三遍。
>老人称:‘风里听见了一声谢谢。
’**
他又翻了几页,每一条都带着泥土的气息与泪水的温度。
“这些该让更多人看到。”
他说。
“已经在做了。”
“闻”
点头,“已有十几个城镇设立了‘记忆角’,专门陈列这类记录。
还有人在编《民间真史汇编》,打算刻版流传。”
阿启忽然笑了:“我们当初只想教孩子认字,现在倒好,竟撬动了一整座历史的大厦。”
“大厦?”
“闻”
摇头,“不如说是掀开了盖在井口的石板。
下面的东西还在往上爬,有些人看见了吓得转身就跑,有些人却跪下来伸手接他们上来。”
第二天清晨,两人分道扬镳。
“闻”
北上燕州,要去参加一场跨郡的“记忆对话会”
,据说会有曾经的加害者后代与受害者家属面对面讲述家族秘史。
阿启则继续南下,前往岭南,那里有个渔村世代供奉一口“哑钟”
,据传是百年前某位被割舌的渔民所铸,从未响过。
临别时,“闻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