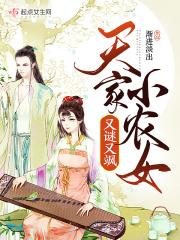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>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(第6页)
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(第6页)
冬至那天,他终于回到故地。
学堂已焕然一新,庭院中竖立着一座环形碑墙,由全国各地送来的碎陶、残砖、旧瓦砌成,每一块上都刻着一个名字。
馆内设有“倾听室”
,访客可在静谧中戴上特制铃饰,尝试感知先人的情绪与记忆。
还有“对话廊”
,陈列着加害者与受害者后代共同签署的和解书。
孩子们依旧来上课,但课程不再是识字,而是“如何面对真相”
。
阿启没有惊动任何人,悄悄走进地窖,打开当年封存的木匣,取出那卷《草芥录?终章》。
他将其置于馆中央的展台上,旁边放上新写的附篇:《归途纪事》。
当晚,他做了一个梦。
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广袤平原上,四面八方皆有人行走,每人手中提一盏灯,灯下挂着一口小铃。
他们互不相识,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。
远处,一座新的高塔正在建造,不是为了镇压,而是为了?望;不是为了播音,而是为了收集声音。
塔顶悬着一面巨镜,映照出万千灯火,如同星河倒垂。
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:“你曾问大地还能不能长出粮食。
现在你看??它不仅长出了麦穗,还开出了花。”
他醒来时,窗外雪落无声。
但他知道,这世界已不再寂静。
翌日清晨,第一批访客到来。
是一群小学生,在老师带领下前来参观。
他们走到展台前,仰头看着《草芥录?终章》的竹简。
一个小女孩问:“先生,这个人是谁?”
老师答:“他叫阿启,是第一个敢教我们说真话的人。”
孩子们齐齐鞠躬。
阿启躲在廊柱后,静静看着,没有现身。
他知道,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记住已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那四个字已被读懂:
**草芥称王。
**
他转身离去,背影融入晨光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某间教室里,一名少年正提笔写下日记:
>“今天老师讲了‘寻名运动’。
原来我们能自由说话,是因为曾有人不怕死地坚持要说。
>我决定,以后每年清明,都要为那些没人记得的人烧一炷香。
>即使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,我也要说一句:
>??我记得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