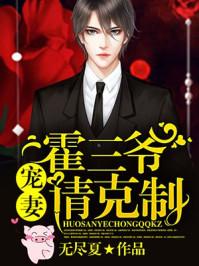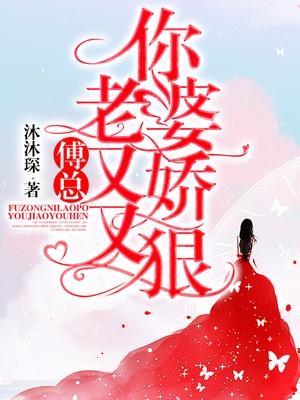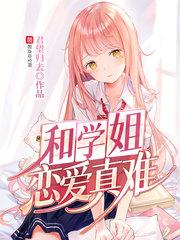笔趣阁>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> 第133章 杨灿是墨者(第1页)
第133章 杨灿是墨者(第1页)
“回禀公子,属下二人在吴州待了十多天……”
其中一名探子抱拳躬身,正要细说,目光无意间扫过立于于睿身侧的赵腾云和刘波,声音突然顿住。
于睿会意地一笑,朗声道:“赵统领和刘先生都是我最信任的。。。
暴雨过后,山道泥泞如浆,阿启拄着一根枯枝缓步前行。
脚底打滑数次,裤腿早已沾满湿泥,像从地里爬出的农人。
他却不急,每一步都踏得沉稳,仿佛这山路本就是为行走而生的经脉。
远处峰峦叠嶂,云雾缭绕,偶有飞鸟掠过林梢,划破寂静。
他的背影瘦削却笔直,如同那日在西岭村讲台上未曾弯下的脊梁。
抵达边境小镇时,天色将暮。
回声驿站坐落在半山坡上,由几间旧砖房改建而成,屋顶架着一面锈迹斑斑的卫星接收器,墙边堆着成箱的磁带与手稿。
沈兰正坐在门前小凳上晒药草,见阿启归来,颤巍巍起身,眼角泛泪:“您回来了……我们都在等您。”
“我来了。”
阿启轻声道,目光落在她手中翻晒的一叠信纸上,“那些信,都整理好了?”
沈兰点头,引他入内。
屋中昏暗,唯有油灯摇曳,照亮四壁悬挂的照片??全是逃亡者、失踪者、被噤声者的面容。
一张张脸沉默地注视着来人,仿佛在等待一句迟来的回应。
她从柜底取出一只铁皮盒,打开后递上一沓泛黄的信笺:“这是最后一批‘音核’监听记录的抄本。
当年他们用这些纸页记下每一句‘危险言论’,如今反倒成了证明存在过的证据。”
阿启接过,指尖抚过字迹。
那是用极细的钢笔写就的速记体,密密麻麻,如蚁行于叶。
其中一页赫然写着:“七月十二日,村民李大柱酒后言:‘三年饥荒饿死万人,为何史书不载?’判定为反动言论,上报处理。”
另一页则记:“学生周念问老师:‘如果课本说的不对,我们该信什么?’列为思想隐患,观察期六个月。”
他闭目良久,再睁眼时,声音低而坚定:“把这些也录入《众声录》吧。
不是为了控诉谁,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,曾有人因一句话消失,也有人因一个问题觉醒。”
沈兰哽咽:“可……有些人连名字都没留下,只有编号。”
“那就写‘无名氏’。”
阿启说,“但要在后面加一句:‘他曾说话,故他存在。
’”
当夜,驿站灯火未熄。
两人并肩伏案,逐字誊抄。
窗外风雨又起,雷声滚滚,似天地也在倾听。
至子时,忽闻屋顶广播机发出轻微嗡鸣??是自动接收到了某段跨境信号。
沈兰急忙调频,耳机中传来断续女声,带着浓重南洋口音:
>“……我是陈婉清,在马来亚槟城。
父亲陈文彬,原为省报编辑,一九六七年被捕,罪名‘篡改宣传口径’。
他没活到平反那天。
临终前对我说:‘告诉中国人,我不是叛徒,我只是说了真话。
’
>我今天寄出他的日记残页,共十七张。
若有谁读到,请替我在碑墙上刻下他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