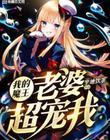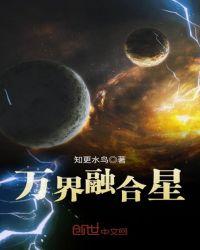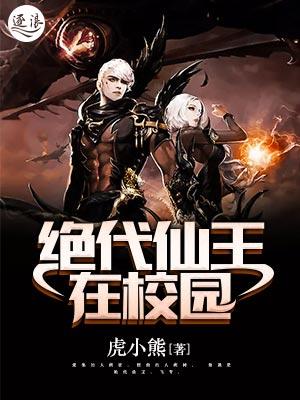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三国: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> 第156章 是人是鬼都在秀(第2页)
第156章 是人是鬼都在秀(第2页)
司马炎默然良久,终下令暂缓军事行动,改派一位“怀柔之臣”前往安抚。
数月后,新任使者抵达。此人名为张俭,原是颍川名士,因直言触怒权贵贬谪西南。他入境后并未张扬,而是微服走访村落,亲眼见到:田亩均分、水利畅通、学堂林立,妇孺皆识字,老者得赡养。更有奇者,村中设有“轮值亭”,每月由不同家庭轮流值守,负责调解纠纷、登记户籍、上报灾情,竟无一人贪渎。
他问一村正:“你们为何如此守法?”
村正答:“因为我们知道,法不是管我们的,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。”
张俭归朝后上疏万言,称南中“虽无城池之固,实有民心之坚;虽无甲兵之利,自有道义之威”。并建议朝廷承认其自治地位,设“南中学政使”一职,专司文化教化,不涉民政。
此议虽未立即施行,却在士林引发巨大反响。北方饱经战乱的儒生纷纷南下,欲亲眼看一看这个“不用刑罚而治”的奇迹之地。
又三年,晋室渐稳,开始推行“占田制”“课田令”,试图恢复农业。然各地豪强勾结官府,兼并土地,农民逃亡日众。唯有南中,仍坚持“共耕制”:每户授田有定额,超耕不加税,荒废则收回;水利设施由集体修建,收益按劳分配;若有天灾,则启动“互助社”调粮赈济。
这一年春荒,中原饥民数十万涌入荆州、益州边境。晋廷束手无策,只得默许地方自行安置。南中七十二部闻讯,自发组织“救荒联盟”,开放仓廪,接纳流民五万余人。
孟琰亲自主持安置事宜。他在义州北郊划出百顷荒地,命名为“新民屯”,实行“三年免赋、五年分红”政策。每户流民分得二十亩熟地,配给种子、农具,并由本地农户结对帮扶。
更有甚者,守心书院开设“难民学堂”,专教识字、算术与耕作技术。许多流民子女第一次拿起笔,写出自己的名字时,跪地痛哭。
一位老儒目睹此景,慨然叹曰:“三代以下,未见此仁政也!”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理解这份坚守。
一日,一名年轻士子从洛阳归来,拜见孟琰,言辞激烈:“先生高义,世人敬仰。然天下分裂已久,晋虽粗定,民心未附。先生拥重资、握众望,何不乘势而起,割据自立,或可兴复汉室?”
孟琰听罢,久久不语。良久,他领那士子登上当年牛金常去的高峰。
山风猎猎,云海翻腾。
“你看那边。”孟琰指向北方,“战火未熄,饿殍载道。再看脚下,孩童正在学写‘人’字。你说,此刻最要紧的是举起旗帜,还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人?”
士子低头。
“昔年牛公教我,真正的功业不在开疆拓土,而在让每一个普通人活得有尊严。”孟琰缓缓道,“我们不做帝王梦,因为我们知道,一旦踏上那条路,就会忘了初心。今天我们可以为民请命,明天就可能变成新的压迫者。”
他转身凝视青年:“你要复兴汉室?很好。但请记住,若你心中的‘汉’只是一个名字、一座宫殿、一面旗帜,那它早已死了。真正的汉,在这千顷良田里,在这琅琅书声中,在每一个愿意为他人点灯的人心里。”
青年恍然大悟,伏地叩首,泪流满面。
十年过去,孟琰年逾古稀,两鬓如雪。他不再主政,退居书院,每日讲学、抄书、教童蒙。但他定下的制度仍在运行:每年一度的“大议政”如期举行,乡议会换届选举公正有序,判议团审理案件透明公开。
景熙八年春,孟琰病重。临终前,他召来诸弟子,问:“若我死后,有人借我的名号揽权专断,你们当如何?”
众人沉默。
一小童怯生生答:“那就……再开一次公审大会。”
孟琰笑了,眼角流出一滴清泪。
“好孩子……记住,没有人可以代表真理,只有制度能约束权力。”
当日黄昏,他安然而逝,手中紧握那本磨破的《牛公言行录》。
葬礼简单至极。依照遗嘱,不立碑,不设祠,骨灰撒入义州河中。唯有那把铁斧,被郑重移入新建的“守心堂”,置于高台之上,四周环绕着七十二部联名签署的《南中约法》抄本。
多年后,一位旅人路过南中,在村塾中听见一群孩子齐声诵读:
>“心中有田,行中有矩,
>言必信,行必果,
>宁做一寸土之耕夫,不为千里江山之君王。”
他问先生:“此为何书?”
先生微笑:“这不是书,是我们每天醒来都要记得的事。”
春风再度吹过田野,稻浪起伏,如同大地的呼吸。那把斧头静静伫立,锈迹斑斑,却比任何刀剑都更锋利??因为它斩断的,从来不是敌人的头颅,而是愚昧、贪婪与专断的根脉。
在这片土地上,英雄不会被神化,因为他们知道,真正改变世界的,从来不是某个伟人的一时壮举,而是千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与选择。
犁铧翻土,书声琅琅,炊烟袅袅。
文明的火种,就这样在平凡的日子里,悄然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