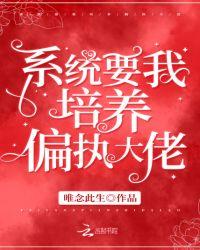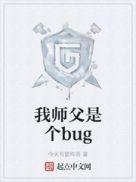笔趣阁>三国: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> 第165章 我又不欠他们的(第1页)
第165章 我又不欠他们的(第1页)
整个德阳殿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。
只见牛憨大步出列,朝御座方向抱拳一礼。
他那双铜铃般的眼睛澄澈见底,目光坦然如初:
“陛下,太后,殿下。”
“当年在洛水边,是殿下将俺从鬼门关拉。。。
春风如针,刺破北方冻土的硬壳。代郡山脚下的小村,炊烟重新升起,不再是灰白断续的一缕,而是连成线、织成网。那绣着“继续”二字的书包被挂在学堂门楣上,成了村中第一面不带姓氏的旗帜。孩童们每日进门先抚一抚那粗线缝出的字迹,仿佛在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击掌为誓。
沈青娥站在新修的议事亭边,左袖随风轻摆。她右臂虽废,却已学会用左手执凿,在石板上刻下《水渠共管约》九条。玉喃蹲在一旁调制石灰浆,低声念道:“第七条:用水高峰时,按户丁数轮灌,不得私开暗口。”话音未落,几个孩子围上来,争着背诵:“谁偷水,罚三日挑粪;若累三次,取消秋收分粮资格!”稚嫩声音里没有惧怕,只有理直气壮的秩序感。
“他们记得比大人快。”玉喃笑。
沈青娥点头:“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规矩。不是压下来的律令,是长出来的道理。”
就在这时,远处尘土扬起,一辆牛车缓缓驶来,车上堆满麻袋,印着江陵屯田区的火漆封记。赶车人跳下车辕,竟是李昭派来的老农工头赵五。他抹了把汗,从怀里掏出一封泥封信件:“李先生说,今年春种早,南中送来的‘耐寒稷’种子先紧着北地。这一车是试种样种,另附《育苗手册》三册,还有一张你亲笔写的防疫口诀拓片??他说要挂在每村学堂墙上。”
沈青娥接过拓片,指尖微微发颤。那是她三年前在守心堂抄录的《发热三查法》,如今竟被千里之外的人郑重传递,如同圣物。她忽然想起赵师兄临终那夜说的话:“医者真正的药方,不在纸上,在人心里扎了根才算活。”
当晚,议事亭点起油灯,村民齐聚。赵五当众拆开麻袋,倒出金黄细长的谷粒,在灯下泛着青铜般的光泽。“这叫‘赤穗稷’,南中三年选育,能在霜后十日仍抽穗结实。种法也不同,需浅沟密植,辅以草木灰拌土。”他一边讲解,一边展开那本手绘图解的小册子,纸页已磨得起毛,显然已被翻阅无数遍。
一位老农捧起一把种子,眯眼细看,突然老泪纵横:“我爹死在饥年,手里攥着半碗观音土……要是早二十年有这个,何至于……”
话未说完,满屋静默。唯有灯花噼啪一声炸响,像是大地深处传来回应。
三日后,第一批秧苗入土。沈青娥亲自带队勘测水脉,用南中传来的“水平仪”校准沟渠坡度。那仪器不过是一根中空竹管注水而成,两端玻璃泡观测水位,却让村民们惊为天工。一个少年惊叹:“原来平地也能看出高低!怪不得以前总淹东头不浇西田!”
玉喃笑着解释:“这不是神仙术,是南中一群瞎子、瘸子、聋人一起琢磨出来的。有个盲匠人靠听水流声定坡度,整整试了七十三次。”
消息如野火燎原。不到半月,雁门关周边十二村自发结成“联耕会”,推举沈青娥为“技术监”,却不肯称“大人”或“先生”,只唤“阿姐”。她每到一村,必先问三事:可有夜学堂?可建议事亭?可设公共药箱?若有不足,便留下玉喃培训骨干,自己则奔赴下一站。
而此时,建康宫内风波再起。
皇帝将《答天下书》置于朝会案前,命群臣议之。主战派将领王允之拍案怒斥:“此乃明目张胆倡乱!所谓‘账目公开’,实为煽动百姓窥探官府机密;‘劳者有份’,更是鼓吹劫富济贫!若任其蔓延,纲常尽毁!”
礼部尚书徐元叹却起身反驳:“陛下,民间已有童谣流传:‘南中有光,照我炕床;北地有墙,遮我饭香。’前日微臣回乡省亲,见族中佃户竟偷偷集资,请人抄录《共耕条例》。他们不怕王法,只怕饿死。”
殿中一时沉寂。忽有内侍急报:冀州刺史自请贬官三级,愿以私财试点“五色账制”,并附万言书陈情:“非臣背叛朝廷,实因去年旱灾,豪强囤粮不售,百姓易子而食。今闻南中之法,愿冒死一试,若成,则利国;若败,甘受极刑。”
皇帝闭目良久,终开口:“准冀州三县试行,名曰‘均田实验’,然仍禁提‘南中’二字。”
退朝后,裴景徽独留殿外,跪伏不起。皇帝回身,见他手中捧着一块陶片,上刻稚拙文字:“我娘说,等有了五色账,就能知道官爷有没有多吃多占。”落款是一个名字:小石头,八岁,代郡人。
“这是今晨由信鸢送达的‘民声帖’之一。”裴景徽哽咽,“南中不派兵,不夺城,只送纸、送种、送理。可这些孩子写的字,比千军万马更重。”
皇帝凝视陶片,良久轻叹:“朕即位以来,所见奏章皆言权谋、兵事、赋税。唯独这份,说的是人心该怎么活。”
与此同时,敦煌方向再传佳音。丝路共耕联盟正式立约,三国使者在疏勒王庭焚香盟誓,以粟特古语、汉文、龟兹文三体镌碑于城门:“自此以往,商路不止通货,亦通仁政;驼铃所至,饥者得食,病者得药。”更令人振奋的是,联盟首任监察使竟是一名曾被贩卖为奴的汉人女子,名唤柳七娘。她在宣誓时朗声道:“我曾在西域被人当牲口买卖,今日站在这里,不是因为谁恩赐,是因为我们共同立下的规矩护住了我。”
南中守心堂收到捷报当日,阿?召集判议局紧急会议。议题不再是“如何传播”,而是“如何应对大规模响应”。
“我们原本以为要走三十年。”孟云摊开地图,指尖划过十二州标记,“但现在,三个月内,已有四十七地出现自发组织的‘共耕小组’,二十处设立平民议事会,甚至有人模仿我们的信鸢系统,组建‘飞鸽传书队’。”
账房科主事忧心忡忡:“可我们也收到情报,王允之已在调集暗卫,准备对北方‘染红之村’实施清剿。他称这些村子‘心向叛逆,形同谋反’。”
阿?沉默片刻,忽然问道:“岩桑前辈可在?”
话音刚落,老人拄斧而入。铁斧上的金线已蔓延至整柄,斧刃竟隐隐透出温润光泽,宛如活物呼吸。他将那片金属鳞片置于案上,众人细看,发现其上纹路竟在缓慢变化,新增三点红斑,正对应幽州、凉州、兖州三地。
“它在感应。”岩桑低语,“每一处民心动向,都化作它的血脉。这不是兵器,是千万人意志的结晶。”
阿?深吸一口气:“既然如此,我们就不再藏了。发布《第二号萤火包》??内容为《民议亭建设指南》《基层议事规则》《防打压自救策略》。这一次,不限区域,全境投放。”
有人惊呼:“这等于直接挑战朝廷权威!”